春節交通擁堵向小城市蔓延 規劃法治化不足是主因
堵車,已經成為社會發展、城市建設的攔路虎。另一個可見的事實是,這幾年,管理部門在不斷尋找治理道路擁堵的辦法,但收效甚微。為何堵車?如何破解?這樣的議題雖然看上去老舊,但時刻與社會發展、個人生活息息相關。在“世界無車日”到來之際,《法製日報》記者走訪群眾與業內人士,試圖找尋破解堵車之道。
交通擁堵“無處不在”
“我也是好心,不是故意走這條路的。”
“你就是瞎走,進死胡同了吧。”
9月19日18時,一場爭吵,被嬰兒的一聲啼哭打斷。然而,爭吵留下的“火藥味”讓這輛車內空間本不算狹窄的SUV顯得異常憋悶。
開車的是男主人顧剛,副駕駛坐著女兒顧媛,後排則是已晉升為姥姥的女主人潘平,剛滿10個月的外孫女橘子在潘平身上焦躁不安。
一家人從北京市昌平區北安河采摘歸來,卻遇上了北京周末的大堵車。
從16時50分開車,這家人已經在車廂裏“憋”了將近1個多小時。
此時,他們的地理坐標位於北京市新街口附近,距離南四環的家還有超過一半的路程沒有走。
“真的是一種煎熬。”回憶起這樣的路程,顧媛苦笑著說。

另辟蹊徑的“死胡同”
9月19日17時48分,北京電視台新聞頻道播放實時路況:行駛緩慢路段42條,東西二環北段方向以及北二環內環均呈現嚴重擁堵路況。
此時,顧剛的車正被“停”在德勝門附近。
昌平區北安河——京藏高速——北二環——西二環——位於南四環中路的家,這本應是顧剛最為便捷的回家路線。不過,鑒於G6京藏高速的堵車“神話”,顧剛選擇從出發地背道而馳向北駛入G7京新高速,之後兜一個大圈再駛入北京城區。誰知,在德勝門,顧剛的車還是被“叫停”了。
看著前方一串車尾燈,顧剛決定“冒險”另辟蹊徑,駛入新街口外大街,向南進入趙登禹路,避開已經擁堵不堪的北二環和西二環。誰知,新街口外大街不到3公裏的路程,顧剛走了將近40分鍾。
“眼看前麵就是紅綠燈路口了,但就是過不去,一個綠燈也就過兩三輛車,我大約等了十多分鍾,家人埋怨我瞎走,誰能理解我這個司機最累啊。”顧剛的話語中充滿了無奈,“可你說這堵車賴誰啊,大周末天氣這麽好,大家都想出行,總不能不讓大家出門吧。”
幾乎在同一時間,出租車司機老王正被堵在北京市朝陽區大望橋南側200米處,前後是看不到盡頭的車龍。老王的車前方30米處,是一個自行車道與機動車道的連通口,從自行車道上擠過來的一輛甲殼蟲,正努力把車頭塞進來。
在老王的出租車前後左右,都是試圖加塞的車輛。15分鍾後,老王仍在原地。
“每天跑活兒8個小時,得堵上4個小時。”
最近幾年,開了十多年出租車的老王親身感受到“首堵”的魔力。遇上前往國貿CBD或者路經長安街等擁堵路段的客人,老王總是謝絕生意。
交通燈紅了又綠,綠了又紅,車流沒有絲毫前進的跡象。老王索性關了發動機,打開交通廣播聽起來。
在老王看來,坊間倡議的“單雙號限行”並沒有傳說中那麽美。因為一些有錢人家,基本都有兩輛以上機動車,單、雙號都有,“可以換著開”。
另一個治堵建議更讓老王無奈。他堅決反對北京仿照上海競價拍售牌照。“你看看滿街的車,有幾輛車的價格超過10萬元?要是買一個牌照就要幾萬元,有剛性需求的老百姓怎麽辦?”說到這裏,老王語速明顯加快了許多。
老王是一名出租車司機,同時是一個私家車主,他對北京未來的治堵充滿期待,常和其他出租車司機聊起未來。
“改變城市規劃是最根本的,但是花的時間太長了。”老王終究先要麵對堵車的現實。頭發中已有不少銀絲發的他指著一輛在快速通道上蠕動的快速公交車,笑著說:“就這蝸牛爬的速度,也叫‘快速’公交?”
不過,對於老王、顧剛等駕駛員來說,更為艱巨的考驗還在後麵。根據北京市交管局發布的提示,中秋節臨近,“最堵9月”將迎來“最堵一周”。
小縣城的“大城市病”
被堵,幾乎是絕大多數居住在城市的人都要麵對的一種現象。堵車正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因為堵車,尤其在北京,人們會將出發時間至少提前半小時;因為堵車,必須要選擇躲避早晚高峰時段出行;因為堵車,人們很可能會放棄不少活動……
而堵車,現如今已不再是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專利”。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和城市規模擴大,“堵車”這一“大城市病”正快速從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傳染”。
“中小城市堵車的速度一點也不亞於GDP增長速度。”在江蘇省南京市一家藥業公司工作的李凱說:“南京上班時間早晨六點半就開始堵,一些重點路段200米路程開車要走20分鍾,‘大城市病’在這裏傳染得很快。”
在縣城甚至是鄉村,堵車也成了當地人揮之不去的心病。
小孫的老家在河南省南召縣,縣城規模比較小。在小孫的記憶中,縣城裏的私家車沒有幾輛。今年春節,小孫從北京回老家,他發現,滿大街的私家車,將縣城堵得水泄不通。
“縣城主幹道叫人民路,從南到北不過4公裏,春節期間幾乎天天堵車。開車走一趟,經常需要半個小時。最堵的一次,我在一個岔路口被堵了30多分鍾。以至於到後來,出門幹脆放棄開車。”小孫說,不光縣城裏堵,出縣城的道路也堵。正月初三,是走親戚的日子。出縣城不到10公裏,到達白河店大橋處,汽車排成了長龍,1公裏長的橋麵變成了停車場。等待1個多小時,汽車挪了不足200米。後來才知道,因為兩輛車發生事故長時間占著道路,導致當天堵了兩個多小時,近千輛車出行受到影響。
上網查閱,記者注意到,小孫的遭遇絕非個案。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雲中認為,中小城市和鄉鎮出現擁堵,一方麵是機動車數量增長較快,現有的道路設施難以滿足行車需求,另一方麵在於道路管理落後,各種車輛混行。
南召縣車管所一名工作人員分析說,縣城堵車最主要的原因是車多了。2014年,僅通過縣車管所入戶的家用型轎車有1000多輛,實際新增車輛遠超這一數字。一個最直接的感受是,縣城也開始出現停車緊張的情況。一到晚上,城區部分道路兩邊停滿了車,一些老小區院內還得搶車位。春節期間,大量外地車輛湧入縣城,超出了縣城本身的承載能力,堵車就在所難免。
誰是城市暢通“殺手”
今年春節期間,一篇題為“一個新聞民工的返鄉手記”的文章在網上瘋傳。這篇文章生動描寫了河南省鄧州市某鄉村的堵車場景:“在村小學一百米外,村村通公路在小河邊折了一個大概120度的彎。春節幾天,這個彎經常堵車。最長一次堵了有300多米,連電動車都擠不過去。”
由此,人們發現,堵車,已經不僅僅是“大城市病”了。
“目前的現狀是,一些小城市比北上廣這樣的城市堵得更厲害。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作為大城市,北上廣等城市的規劃者在城市規劃時多少考慮了一些城市擁堵問題,隻是沒有考慮周到。而許多小城市在當初規劃時,交通問題幾乎沒有被考慮在內。”交通運輸部交通幹部管理學院教授張柱庭在接受《法製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城市規模盡管不同,但在擁堵問題上是沒有本質區別的。
交通擁堵“病根”何在
在張柱庭看來,堵車是典型的“城市病”頑疾,多種原因綜合造成了目前大中小城市甚至是縣城、鄉村麵臨的擁堵問題。
“第一個層麵,按照時間因素可以歸結為曆史原因和現實原因。從曆史原因來看,一些曆史老城,早年間在城市規劃設計時沒有考慮到這麽大數量的機動車,老舊的城市路網顯然滿足不了目前的行車需求。”張柱庭說,這個問題在北京很明顯,“麵對曆史原因,我們不能抱怨過往的規劃者,但是現實原因,比如現在的城市規劃、管理等現實問題則是要有批判精神的”。
張柱庭說,第二個層麵是本質問題和表象問題。城市擁堵的本質問題是城市土地供給總量和對城市土地需求之間的矛盾。
“城市規模是一定的,盡管可以往外拓展一些,但是土地總量有限,而社會對土地的需求是無限的,城市的各種需求都希望土地能夠滿足其要求。城市交通對土地的需求同樣也很大,但是,我們沒有給城市的土地需求定一個規矩,工業建設、商業建設都需要用地,在各種用地中,交通用地應當占到什麽樣的比例,這是根本問題。麵對這個矛盾,我們並沒有提前立好規矩。”張柱庭說,對於一些決策者來講,交通用地的現實收益很差,建設城市道路不能很快從中獲利,建設公共停車場也很難從中掙到錢,交通用地更多的是一種劃撥用地,不能夠獲得土地經濟效益最大化,它的效益分散給整個社會群體,往往就會犧牲一部分公共利益。
“我主張各類交通用地至少要占到城市用地的20%,這一部分是每個人都應當享用的。”張柱庭說,除此之外,路網規劃不到位也是造成擁堵的重要原因之一。全國很多城市的規劃都患上了一個“毛病”——“攤大餅”式的規劃,實行環路交通。環路,就是在路途中繞很多路才能到達。最後,環路成為城市的“堤壩”,隔斷了城市的連接。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支振鋒則認為,交通擁堵是人與空間矛盾最鮮明的體現,車輛的快速增長與道路的有限拓展難以協調,早晚高峰潮汐出行的動態縮放與城市道路空間的靜態穩定無法匹配,都會導致交通不暢甚至滯塞。
“因此,說到底,交通擁堵的首要原因是車輛太多、增長太快,而城市規劃建設的不科學、公共交通設施資源的不充分、公共服務分配的不均衡、貪大求全模式的無序化、交通出行參與人的不文明,都是城市暢通的‘絕命殺手’。”支振鋒說。
治堵不能顧此失彼
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一些城市管理者,特別是北上廣深等特大型城市的管理者一直都在治理擁堵。
查詢相關資料不難發現,相關部門的手段和措施有許多,但主要不外乎兩種:一是“限”。先是限行,按一定規則限製機動車出行,以減少存量機動車上路行駛;再是限牌,在限行措施作用不明顯的情況下,通過拍賣或搖號的方式控製機動車增量。
第二種治堵措施是“漲”。通過上漲停車費等與機動車使用相關費用,增加車輛使用成本,以此倒逼車主減少機動車出行。
在爭議中前行的“限、漲”組合拳,在局部範圍內對交通擁堵有一定效果,但似乎難以從根本上扭轉交通持續擁堵的狀況。
以北京為例,2004年至2014年,北京機動車保有量增長330萬輛,較10年前機動車量增幅近160%。其間,北京大力發展公共交通,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從29.4%提高到48%,全路網工作日交通擁堵指數比2007年下降23%。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表示,雖然北京交通發展取得很大進步,但交通出行品質有待提高,道路堵、停車難、公交慢、地鐵擠、換乘不便等問題仍很突出。
前不久發布的《2015年第二季度中國主要城市交通分析報告》顯示,北京依然高居擁堵城市榜首。
在張柱庭看來,解決擁堵問題並非一籌莫展。
“我主張用製度確定交通的地位,建立‘交通影響評價製度’,要扭轉過去交通處於被動的局麵。在進行小區、大型場館建設前,必須進行交通評價,審批後才能建設,要建立‘城市交通、公共交通引領城市發展’的概念,不能讓交通去適應城市發展,要依靠公共交通引導城市發展。”張柱庭說,城市道路應該規劃為“網格狀—立體化”,所謂“網格狀”就是東西南北應該互通,交叉的地方“立體”起來,空間、地表、地下綜合利用,“這才是理想的交通規劃”。
支振鋒建議,車輛暴增雖然是首要原因,但從根本上說,交通擁堵考驗的是城市治理水平,因此,改善城市規劃建設、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優化城市發展模式,才是治本之策。
針對城市交通的規劃問題,張柱庭的建議是:城市交通是個複雜的係統工程,與城市建設、功能區分布、交通路網設計、公共交通供給、治理價值取向等息息相關,不能顧此失彼,迷失方向。
“同時,規劃要充分聽取公眾意見,並強化規劃的剛性約束力。這是規劃法治化非常重要的方麵,沒有約束力,無異於形同虛設。過去許多城市建設和交通規劃並不是本身不好,而是剛性不足,變化太快。即使是通過嚴謹的法定程序審議批準的規劃,也很容易因一人一事一時而發生改變。”張柱庭說,在很大程度上,城市今天的擁堵,表麵上是車輛增加的結果,背後實質上是過去城市建設和交通規劃法治化程度不足引發的問題。因此,在公眾充分參與的情況下編製科學的城市建設和交通規劃,不僅不能輕易改變,而且還要對違法變更行為施以嚴厲製裁。唯有如此,規劃的權威才可以維護,交通擁堵的治理也才有希望。
公交優先是根本出路
今年7月底,周正宇在交通運輸部官方網站進行訪談時提到,到2020年,北京力爭基本建立現代化綜合交通體係,城中心公共交通通勤時間平均60分鍾,高峰時段中心城交通擁堵指數降至6以內,總體狀況保持在輕度擁堵狀況。
據介紹,北京市在城市區域交通方麵,將實現區域交通和城市交通有機融合,航空、鐵路、公路等交通方式協調發展,區域交通暢達高效。形成北京為中心50公裏半徑範圍內的“1小時交通圈”。北京在公共交通方麵,構建多層次、多樣化的公共交通服務體係,中心城公共交通出行的平均通勤時間不超過60分鍾,也就是說五環內上下班時間不超過1小時。
這樣的設想,和張柱庭的主張不謀而合。
作為業內專家,張柱庭向《法製日報》記者介紹說,治理擁堵還涉及科學管理問題。
“交通擁堵在很大程度上是車輛需求與交通供給的矛盾。在交通供給已經固定的情況下,就要建立以公共交通為主的體係,‘私人車’也就是運輸人數少的車要受到限製,在這個管理體係下要設立一些公共交通優先的製度。”張柱庭說,同時,這個製度還要網絡化,要給予更多的公共交通配置資源,比如北京的地鐵,現在已經能夠達到這樣的水平,但是地麵交通顯然還沒有達到。
在張柱庭看來,有關公共交通綠色出行方麵的概念人人皆知,但行動顯然不夠。導致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一方麵是宣傳的空泛化,另一方麵是缺乏綠色出行的基礎條件,比如自行車道缺失或被擠占,公共交通不舒適甚至缺乏起碼尊嚴、電動自行車售價昂貴等。要想真正推行綠色出行,就需要政府部門真正下大力氣建設轉乘停車場、打通公交係統的“末梢神經”,增加公交車的舒適性和方便性,降低電動自行車的購置成本,提高人力和電力通行的便利性等。
張柱庭建議,在交通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難以滿足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全部需求,法律政策應當更加關注公共交通發展。他說:“把路權更多地劃給公共交通,這是政府部門解決交通擁堵的根本出路。所以我主張,凡是四個車道的地方,有一個車道從早到晚全天候是公共交通專用道,再有一個車道是在上下班高峰時是公共交通車道,其他車輛隻能在規定時間以外使用這個車道。這樣公共交通的快捷優勢馬上就顯現出來。”
專家認為,公共交通擴容是緩解城市交通擁堵的最主要手段,要開展城市道路建設、發展新興的地鐵和軌道交通,加大公共交通的運力投放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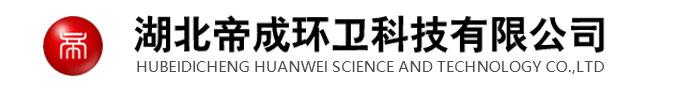
 公司簡介About Us
公司簡介About Us 新聞中心News
新聞中心News 谈球吧-体育赛事中心Products
谈球吧-体育赛事中心Products 谈球吧-体育赛事價格Products Price
谈球吧-体育赛事價格Products Price 訂車流程Process
訂車流程Process 售後服務Service
售後服務Service 客戶留言Messages
客戶留言Messages 聯係我們Contact Us
聯係我們Contact Us



